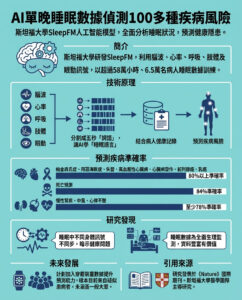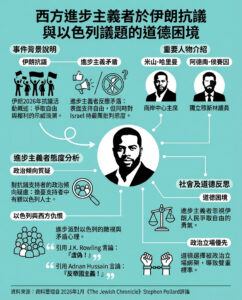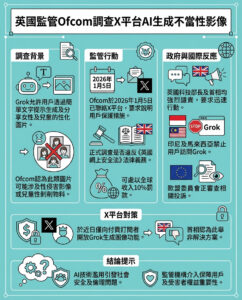AI、恐懼與設計未來:慌張絕非創意之源
設計界領袖Brian Collins在他最新的Designism專欄中指出,面對AI帶來的變革,創意人應該停止過度擔憂,開始想像那些尚未存在的可能性,因為最傑出的作品依然需要人類獨有的靈魂。
讓我們先說清楚:這並非危機。
真正的危機,是中央公園地鐵站淹水、客戶在週日晚上打電話,或者我心愛的《Ziggy Stardust》專輯被刮花。
而現時大家對機器能比一般人更快製作平庸藝術的恐慌,只是「害怕新事物」這部長篇悶劇的最新章節。
沒錯,有人不滿,動畫師抗議,藝術家打官司,一些設計師抓緊自己的「珍珠」彷彿Proxima Nova字體突然被禁用一樣。大家擔心機械人會搶走我們的工作、點子,甚至品味。
拜託。
如果品味是做創意工作的必要條件,那大部分作品根本不應該存在。別裝作門檻曾經有多高。事實是,有一個炫目的新工具出現了,結果多數人選擇了恐慌,而非學習使用它。
慌張是最沒有創意的反應。
七年前,勇於嘗試的Chris Do訪問過我,當時我們討論如何在Collins利用生成設計系統。其實,我們早就知道這個時代會來臨。
歷史上,藝術家總是對進步感到被冒犯。相機冒犯了畫家,文字處理器冒犯了小說家,電影冒犯了劇作家,電視冒犯了電影公司MGM,蘋果麥金塔冒犯了排字師,取樣技術冒犯了音樂家,直到他們自己嘗試後才接受。
每代人都堅稱自己遇到的困難是高尚的,而下一代則是在作弊。
在Collins,客戶請我們不是為了新奇,而是為了「不同」。真實、無法忽視、能激勵人的作品——因為這是憑驕傲而非提示詞創作出來的。
機器可以無止境地重混過去,毫無靈魂,但它們看不到我們所見,感受不到我們所感,更絕對無法想像尚未存在的事物。
那是我們的工作。
這裡有個不舒服的事實:AI會讓劣質作品更劣,讓平庸氾濫成災。但對有才華和動力的人來說,它可能變成利器。
我們多年前已開始用編碼字體與算法視覺設計。當時不流行,但我和合夥人Leland Maschmeyer覺得這是必須的。我們嘗試並建立早期生成算法,協助Spotify重新設計與推出,為Type Directors Club創作動態字體,也為舊金山交響樂團、Twitch、迪士尼、Mailchimp、設計學院、Bose,甚至最新的Muse打造活生生且可回應的識別系統。編碼不是附帶想法,而是基礎。這些不只是新奇實驗,而是想像力、結構與未來的演練。
有時結果驚艷,有時則垃圾,就像人類創作一樣。我們學會了何時從AI開始,何時該停止。
創業初期,我們曾與佛教尼姑Pema Chodron一同靜修。她直言:「完全覺醒,就是不斷被推出舒適圈。」
我們明顯已經到了被彈射出去的階段。
現在的變化速度瘋狂,干擾頻繁。但這是凍結不動的理由嗎?當然不是。
這是提醒我們要更敏銳、思考更深刻、計劃更周詳、努力更勤奮的時候。
我看來,機器永遠無法擁有讓最佳設計師不可取代的東西:判斷力。那種能提出改變一切問題的能力,當大家都說「好啦,差不多就行」時,憑直覺說不的勇氣。
知道什麼不該做。
如果你仍然擁有這種能力,好消息是你會沒事。
所以,我不擔心。我見過這一切:歇斯底里、退縮、往平庸奔跑。然後,真正的人才悄悄崛起。
當其他人抱怨、嘆息、控訴時,總有人在創造非凡。
也許那個人就是你。
希望如此。現在,請開始行動吧。
即使被刮花了,Ziggy Stardust也會同意:
「轉身面對怪異……」
—
評論與啟示
Brian Collins的觀點令人振奮且具啟發性。他提醒我們,面對AI浪潮,創意界不應陷入恐慌,而要學會與新技術共舞,把它視為激發創造力的工具,而非威脅。歷史一再證明,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曾引起藝術界的排斥,卻最終催生新的藝術形式和創作方法。Collins強調,人工智能缺乏人類的靈魂與判斷力,這正是創意工作者不可替代的核心。
這種觀點為香港的設計師和創意人提供了重要啟示:面對AI技術的普及,唯有提升自身的判斷力與想像力,才可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創意樞紐,更應該擁抱變革,用科技賦能創新,而非抗拒。Collins的話語也提醒我們,創意不只是模仿和重複,而是要敢於「看到未來尚不存在的事物」,這種敢於想像和拒絕平庸的態度,才是推動設計界持續前行的動力。
總括來說,Collins的文章不單是對AI時代的自我提醒,更是一種對創意精神的呼籲:在變革的浪潮中,唯有保持清醒頭腦和獨到見解,才能打造出真正有靈魂、有價值的作品。這對香港創意產業的未來發展,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以上文章由特價GPT API KEY所翻譯及撰寫。而圖片則由FLUX根據內容自動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