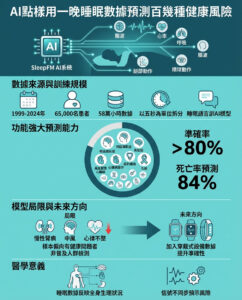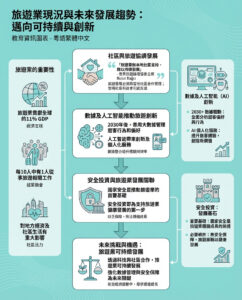藝術家必須停止製造恐慌。人工智能對音樂產業並非威脅
作者:羅賓·米拉爾爵士
人工智能對音樂的威脅程度,並不比1980年代的鼓機更大。那些富裕的藝術家對人工智能的哭訴只是製造恐慌而已。
最近,一小部分極為富有且知名的藝術家聚集在一起,聲稱他們的作品必須受到人工智能的“保護”。這種呼聲讓人聯想到1990年代末期對Napster的恐慌:禁止它!關閉它!
當時的論點是,數字音樂分發會摧毀整個行業。然而,常識最終佔了上風。串流音樂不僅成為了音樂的大眾化工具,還減少了塑料、黑膠和全球分發的環境成本。
人工智能並不是音樂版權的問題
我想澄清:我支持版權。作為一名創作者,我沒有興趣支持任何可能損害藝術家權益或收入的事物。但目前的情況並非如此。
業界某些人推動的誤解是,允許人工智能模型研究和學習廣泛的音樂,等同於盜竊或抄襲。這根本不是事實。如果這些批評者花些時間在人工智能音樂平台上,他們會發現大多數平台已經實施了嚴格的保護措施。大多數平台明確拒絕直接使用或複製受版權保護的材料。
要求停止人工智能模型分析音樂、影像、電影、電視、書籍、醫學研究和建築的訴求,既不實際也不必要。參考資料庫已存在幾個世紀,早於版權法正式化之前。學者、音樂學家、小說家和畫家一直在研究過去的作品,做筆記、獲取靈感並創造出新作品。藝術家們世世代代模仿彼此——有些成功,有些則不然。藝術的演變一直依賴於對過去的重新詮釋。
我們需要的是細緻的思考,而非恐慌
對人工智能的憤怒未能認清這一基本事實。沒有任何人工智能系統在“竊取”凱特·布希的聲音或艾爾頓·約翰的旋律。因為某人使用人工智能生成了與過去相似的和弦進程,他們的收入來源不會因此枯竭。版權法已經足夠應對真正的誤導、抄襲和詐騙案件。防止假冒古馳手袋和假冒iPhone的法律原則同樣適用於音樂。
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並不構成威脅,與1980年代的鼓機或1990年代的數字取樣一樣。這兩者都曾遭到某些業界人士的類似憤怒,但最終都成為了賦權於新一代藝術家的工具。
是的,確實存在風險。我們必須制定明確的指導方針,以確保藝術家得到公平的報酬,並且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不會誤導消費者。但呼籲全面禁令和煽動恐慌並不是解決之道。人工智能並不是創意的死亡,而是藝術家工具箱中的另一個工具。正如合成器、取樣器和Pro Tools曾經是的那樣。
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如何負責任地將人工智能融入創意領域和音樂商業中。這需要的是細緻的思考,而非恐慌。
羅賓·米拉爾爵士是藍雨音樂的創始人及SCOPE的主席。
—
在這篇文章中,羅賓·米拉爾爵士對音樂產業面對人工智能的恐慌反應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的觀點鼓勵我們重新思考如何看待新技術對藝術創作的影響,而不是盲目地抵制或恐懼。隨著科技的發展,音樂產業必須學會與這些新工具共存,並尋找有效的合作方式,以促進創意和創新。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只有擁抱變化,才能在音樂和其他創意行業中持續繁榮。
以上文章由特價GPT API KEY所翻譯及撰寫。而圖片則由FLUX根據內容自動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