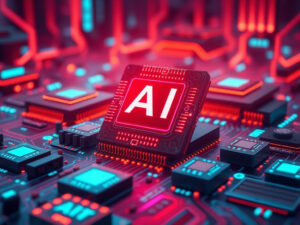大型藥廠在企業財報日表現突出,儘管面對關稅威脅及降價壓力依然超出預期
在周四一個充滿波動的企業財報日中,主要藥廠成為亮點,儘管他們正面對行業特定關稅的威脅、降低藥價的壓力,以及可能削弱未來數年在美國大量投資努力的聯邦裁員,但仍成功超越市場預期。
與航空公司等因關稅不確定性而大幅削減或取消財測的企業不同,主要藥廠大多未受貿易動盪影響。布里斯托爾-邁爾斯斯奎布(Bristol Myers Squibb)、默克(Merck & Co)、賽諾菲(Sanofi)及羅氏(Roche)均在周四公布的季度財報中超出預期,且布里斯托爾更上調了盈利預測。
整體而言,醫療保健板塊較能抵禦市場起伏,今年標普500醫療指數僅下跌0.5%,遠低於標普500大盤指數的7.5%跌幅。
然而,藥廠仍面對多重挑戰,包括特朗普政府縮減聯邦工作人員規模,尤其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人員裁減,以及對藥品進口的調查,這些因素可能為行業課徵關稅鋪路。
目前藥品尚未被納入特朗普的互惠關稅範圍,但他主張美國需要加強國內藥品生產,減少對外國供應的依賴。
雖然關稅的具體稅率和實施時間尚不明朗,但若特朗普推行計劃,藥廠將面臨重大打擊,因為美國每年進口超過2,000億美元的處方藥。
部分公司已開始感受到影響,例如默克預計因美國對部分國家(尤其是中國)徵收關稅,以及其他國家隨後的報復關稅,將承受約2億美元的損失。
默克最大風險來自其暢銷癌症藥物Keytruda(Keytruda是全球銷售額最高的處方藥)。默克表示,現有美國庫存足夠應付今年需求,並正努力擴大未來的國內生產。
強生(Johnson & Johnson)本月早些時候在全年度預測中已計入約4億美元的關稅相關成本,主要來自其醫療器械業務。
製造商表示,若全行業被徵收關稅,可能引發供應鏈中斷,最終影響病患用藥。他們持續與白宮溝通,強調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
布里斯托爾財務總監大衛·埃爾金斯(David Elkins)指出:「我們最擔心的是任何會影響創新,或限制病人用藥途徑的因素。」
從長遠來看,專家認為企業須增加在美國的投資。ING醫療分析師斯蒂芬·法雷利(Stephen Farrelly)說:「明顯有兩條路,一是轉移現有產能,這既困難又昂貴且耗時;另一是將未來投資直接定位在美國,這更可行且現實。」
多家藥廠已承諾投入數十億美元擴大美國生產,羅氏本周早些時候宣布未來五年將投資500億美元,同時將部分現有產能轉移到美國。
不過,羅氏CEO托馬斯·施奈克(Thomas Schinecker)周四表示,若所有供應美國市場的產品均在美國生產,將推高製造成本。他透露,公司正與政府直接洽談關稅豁免,並強調羅氏輸入美國的產品,能用其出口的美國製藥品和診斷產品抵消。
特朗普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與挑戰
儘管藥廠願意加碼美國投資,但特朗普政府裁減FDA審核新藥生產廠房的相關人員,可能阻礙藥品生產的審批流程。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推動的健康機構重組,計劃裁減FDA約3,500名員工,引發外界對藥物和疫苗審批流程受阻的擔憂。
FDA未能在4月1日如期對Novavax的新冠疫苗作出批准決定,激起外界對疫苗是否會獲批的疑慮,直到本周FDA要求補充數據,才讓人看到最終獲批的希望。
默克高層在周四的投資者電話會議中表示,公司藥品審批的FDA時限尚未改變,但仍密切關注FDA裁員對中長期的影響。
此外,藥廠還須應對政府降低藥價的壓力,包括嘗試將美國藥價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的較低價格掛鉤。一些歐洲藥廠正敦促歐盟允許提高藥價,以在特朗普關稅威脅下支持本地投資。
—
評論與啟示:
這篇報道清楚呈現了美國大型藥廠在當前政策環境下的複雜處境。一方面,藥廠財報表現強勁,證明其核心業務韌性及市場需求穩定;另一方面,貿易政策及政府內部重組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正潛藏對產業鏈和創新能力的長期影響。
特朗普政府推動的關稅政策和聯邦裁員,表面上是為了促進本土製造和削減政府開支,但從醫療產業角度看,過於激進的政策可能破壞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增加製造成本,甚至延緩新藥的審批速度,最終損害患者利益。
此外,藥價控制措施雖有助於降低患者負擔,卻可能抑制企業研發投入,影響未來藥品創新。藥廠在美國大量投資擴產的計劃,是否能真正落地,還需克服政策上的種種阻礙。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此局面反映了全球化時代下,產業鏈與政策制定的複雜交織。藥廠既要面對國內政治壓力,也需在國際市場保持競爭力。未來,藥廠如何在維持創新動能、確保供應鏈穩定與應對政策挑戰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業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的難題。
對香港及其他地區的讀者而言,這也提醒我們,全球藥品供應和價格政策的變動,可能會波及本地市場,尤其是在疫情後全球醫療資源重組的背景下。理解這些變化,有助於更好把握醫療健康產業的風險與機遇。
以上文章由特價GPT API KEY所翻譯及撰寫。